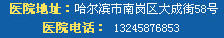以曾鲲化的《中国铁路史》(北平:燕京印书局,)页、国民政府铁道部总务司统计科编的民国22年份中华民国有铁路统计总报告“统计说明”42-43页、支那驻屯军乙嘱托铁道班《平汉铁道调查报告》“经理关系”11页三种资料整理而成的从光绪32年到民国24年的平汉路历年营业收支,从中可以发现,峰值时期()铁路总营收可达元(银元),也就是.万元,而在战乱年份(),收入也达元,即.元,不过运营成本却差不多,例如年成本也达.万元,所以该年净收入仅为.万元,民国9年之后到民国24年间再无比这一数值更小的成本报算;
而在年成本竟然也飙升到.万元,所以当年虽然纸面数据是年以来最好看的,但是净盈余却没有超过之前的最高值,年的.万元,仅为.万元。从各个方面看,纸面营收最高的年份为年,为元;运营支出最高的是年,为元;盈余最高的年份年,为元。
平汉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是-年的北洋军阀管制时期,第二是-年的国民政府管理时期。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是,无论是几次直奉战争,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新军阀混战,其作战均常以铁路为机动运输、补给基础,而中原大战、北伐战争等等,都征用了脚夫、驴子、小车、大车、民船和铁路运输军资和兵员,根据民国15年美国驻天津地区领事馆对于华北平原货运费用调查,上述六种运输方式的运价依次为0.、0.、0.、0.、0.和0.(平均每里1吨(圆)),所以可见真正长途大货量运输如果没有突发情况是不会改用火车之外的其他运力的。W.W.Rostow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指出的降低运价加深了市场一条,实际上和笔者之前在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中所提到的运输供应商或资源的富集造成交易成本下降,从而引发商业交易概率提高,形成交易中心的内容相契合:
笔者有一个推测,即关于上沽岭富国场这样的滨海盐卤之地的行政建制都与内陆纵深的州县和军事管理有关。从日常运行上说,滨海土地盐碱,且常有海浸和永定河、大清河、滏阳河等海河水系直流多、流量大而干流少且短(“肚大嘴小”)造成的结构性水灾,无法稳定种植、产出主粮,所以一般灶户盐工皆依赖内陆粮产稳定的州县;另一方面,中国历朝历代都实行严格的专卖制度,尤其是嘉靖朝创立“引岸专商制度”之前,封建王朝奉行赚取中间价的垄断中间商环节政策,从盐场到卖给具体的专卖商人之前的收购、转运官坨、存储护卫都是官府需要自费的环节,这一切除了不菲的财政养护开销外,维持官盐坨的安全、由盐场到官坨运输的劳力,都需要朝廷自理。因此驻防在盐场附近的兵力和距盐场最近的产粮县共同保障了朝廷对盐场的有效统治。特别是盐产的保守与买卖都是军管,而盐场运行的粮食供应又由行政州县控制,这样就形成了相互牵制,军队和邻海县都无法单独控制盐利的形势,这就是保障了朝廷能有效调动驻防兵力、临海州县、盐场三方任何一者的权威性与灵活性。而当军队想要增强自身在滨海盐务问题上的独立性时,屯田垦荒就成为摆脱行政州县掣肘与朝廷钳制的手段,而朝廷为了保持这个微妙的平衡仍然不能使军队完全控制滨海屯田事务的主导权,于是形成新的行政州县建制,在增加朝廷粮秣田赋收入的同时,又能削弱旧州县在盐场问题上的影响力,形成新置州县与旧州县在供粮问题上的新平衡;同时又建立起驻屯军与新州县之间的运行和守盐问题上的新制约关系。像上古林的富国场,最早归静海县咸水沽管,后来竟迁到运粮和粜盐交通更困难的新出露海滨区的上沽岭;而上沽岭在新海设治局成立前则在天津县与盐山县之间,具体归属虽然不甚明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上沽岭早已不再归静海县管辖;丰财场也几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从葛沽到塘沽,中间在晚清实际上就已迁至邓沽庄南开村一带,葛沽在生产上从一个盐场场署转型为一个粮食生产与南北运输的集散地,而盐务的功能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剥离,盐务重心东移;同时在葛沽设置巡检司这样一个次县级单位,也是行政州县建制化的剥离,使之实际上丧失了对丰财场直接的盐政性管辖权力,而仅仅成为滨海55个村落的保安局。朝廷控制的漕粮和输往内陆引岸的盐运两股运输的刚需使得运输脚力、船运也富集在这两种活动活跃的地区,特别是两者重合的地带。而民间的跨区域贩运商业无非注重两个要点——成本低即运费低,收益高即市场广、购买力强。而贩运供应者众多的地域其运价就更低,商业成本低;贩运汇集、停放密集的地带,能供应的商品种类、数量也比其他地方多,所以交换的动机、概率也大,交易的总需求也比其他地方大,商业利益的增益也就更大。所以说,刚需引发的运输资源配置重心(富集点)的偏移,导致商业交易成本低地的移动,进而带动了区域贸易中心的移动。静海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实际上就是这种交易成本优势的相对丧失。塘沽首先在军事上发挥作用,而且长期南北两岸分治,即便到了大一统时期,朝廷也常常沿河分治与不同州县,北岸先后经历了武清县、香河县、宝坻县、宁河县;南岸先后经历了清池县、静海县、天津县,总的趋势也是县治不断东移,南岸治所有北移倾向,这与西南部的静海移往偏东北的天津卫的趋势是同步的。同时将丰财场人为的分离成南北两片。而且在盐场内部作业过程中,无论北洋、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也仍然以海河为界,分出邓沽与北塘两个片区管理运作,邓沽庄-南开村一线以北到北塘的基础设施投入,到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对河南一边倒的优势。北宁路修建后更加重了这种不平衡状态。本身在修建北宁路时就考虑的是塘沽到天津之间运费的低廉度——偏东北的方向脚力和船力资源配置充足,修铁路的沙石、铁轨等材料运费低;同时建成之后无论是列强商贸还是清廷自胥各庄等地运输军用煤铁,卸货便利与低成本也是河北岸更好,所以没有任何通往河南海滨的铁路规划。乃至日后津浦路修建时直接顺着南运河走,静海以东的河南毫无现代交通建设基础。而火车的运输便利与大运量成本分担,使得北岸对南岸的交通成本优势又呈几何级数增长,南岸的交通劣势“内卷”就日益严重。——《芦台22场:清至民国的静海衰落、海河南岸匪患与“北宁路内卷”》
其实从这个角度上看通政使司刘锡鸿的观点(晚清的铁路辩论反映了幼稚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华的不成功实践)也有可商之处,如果没有一个有开放有保护的二元自由主义政策,使得由母本产业派生出的更先进的子业得以聚拢财富,并将这种财富分流到其它母本行业,促进总需求的增长,是不会造成总生产的增加的,也就不能形成经济的增长。例如仅仅是以原料产业为商业的增长源,那么这种分流也就不会随着分工体系流动,引发全体的需求增长。
相反,由于其他行业的衰退与同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不平衡,总需求甚至有衰退的可能,因此,马若孟(Ramon.H.Myers)的分配理论在年代流行有着理论合理性——由子业盈余通过分工体系浇灌母业,造成总需求的增长,反过来,如果是母业盈余,第一无法浇灌子业,沉淀下来,而这些持有沉淀资金的弟煮、高利贷者为了进一步逐利,只能向盈利行业投资,一是继续扩大地产等原料产业的规模,而是投资盈利的子业,也就是帝国主义控制的工商业,而随着边际效应递减原则的作用,地产的增长达到一个相对停滞状态,那么他就会增加对后者的投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
但是刘锡鸿的论述中也没有排除中国的先进产业发展的情形,因此仍然是重商主义的粗浅认知。在先进产业生成后,只有在需求恒定状态下,这种“经济能量守恒”原则才会成立。需求并非是恒定的,一旦当前收入与一定时段内的收入预期呈现出稳定上升状态,这就会造成需求的稳定增长。正是这种稳定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
因此,产业升级条件下的总需求的增长能够带动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物质条件——这个国家首先是个强国。弱国想依靠完全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的永续增长(自主的产业升级)是不可能的,而且实践上也从未有这样一个强国实现,恰恰相反,实行自由主义政策的英法在二战后就衰落了,而实行不同国家主义的日德美苏都成为二战后国际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先强起来再谈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否则永远是拉美状态。
这恰恰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自证的——分工体系由子业倒灌母业,从国际上看仿佛能够使得原料产业国得到分流,但实际上,这些分流最后又会通过投资回流到子业上,所以实际上真正得到增长的是分工体系上游产业国,而其他国家也就是原料产地的纸面数据增长和产业升级不振,就是由上游国的资本相对富集造成的全球慢性通货膨胀造成的贬值效应和上游产业转移的生产基金扩张,或者说固定资本扩大带来的名义GDP增长实现的。这些增长的物权归根结底还是子业资本所有,而通胀则是子业资本所在国的金融资本先做大后做空的繁荣泡沫工具。说到这也就无需赘述了,这完全不是max的阴谋论,而是英美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明明白白给我们说出来的东西。
因此,铁路的建设本身并不具有倾向性,关键在于铁路是与怎样的配套经济体系衔接的。在英国的综合开发体系中,这种商业中心催激素是有利于分工体系子业普惠母业、增进总需求的;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则是病态臃肿母业,摧残母业其他业者、增强子业外部竞争者进而不利于子业发展、使倒灌效应难以发挥作用的帝国主义吸血管,这是毫无疑问的。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abmjc.com/zcmbzz/2707.html